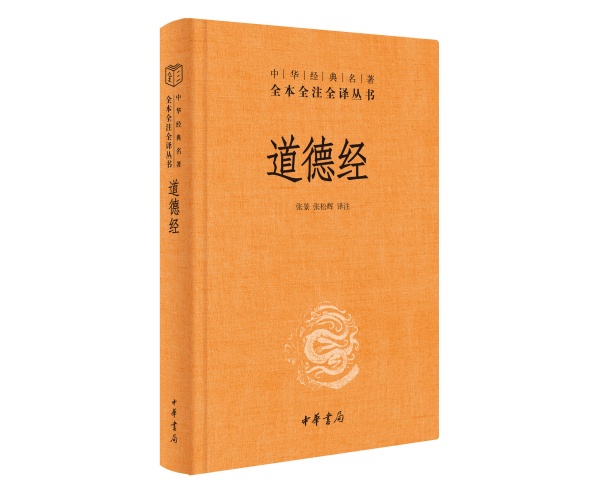上一篇,我们向大家展示了《道德经》的重要主题:无为,解读部分让大家对老子所倡导的顺应自然、不过度干预的理念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今天,我们将把目光聚焦于《道德经》的另外两个核心主题——“宠辱若惊”和“有无相生”,共同探寻老子的辩证思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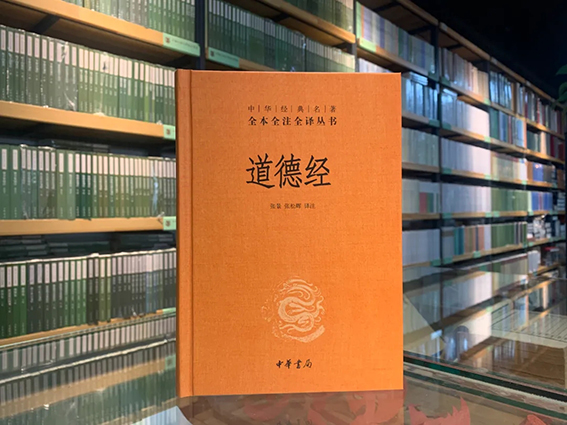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
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上,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解读】
本章自“吾所以有大患者”以下,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解释。任继愈《老子新译》把这一段翻译为:“我所以有大患(虚荣),由于有了我的身体,若没有我的身体,我还有什么祸患呢?所以只有把天下看轻、把自己看重的人,才可以把天下的重任担当起来;只有把天下看轻、爱自己胜过爱天下的人,才可以把天下的重任交付给他。”并在解说词中说:“他(老子)认为有许多麻烦,是由于自己这个人的存在而引起的,为了避免给自己招来忧患,最好不要身体。身体都不存在了,还有什么忧患呢?照这样的逻辑,为了避免牙痛,就不要牙齿,为了不犯错误,就不要工作。”蒋锡昌《老子校诂》和张松如《老子校读》等人的解释、译文基本与此相同。
按照任先生的解释,老子用来解脱灾难的办法就是消灭自己的身体,这不仅在全书找不到根据,而且也殊难想象老子会生出如此愚蠢的办法去解决矛盾。老子在这里讲的完全是有私(有身)和无私(无身)的问题。在第七章中,老子说:“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很清楚,老子是要求人们“后其身”“外其身”“无私”的,至于“身先”“身存”“成其私”则是前者的自然结果。七十八章还说:“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这明明讲的都是治理天下的人应该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是无私的人。就《道德经》全书思想来看,老子也是提倡清静寡欲、无私无我的,这里突然提出要“爱自己胜过爱天下”,明显与全书思想是冲突的。而且按照“后其身而身先”的理论去推理,那么过分爱护自身的结果势必会导致自身难保,老子又怎能提出把爱护自身放在首位的主张呢?特别是老子又怎能提出把天下交给极端自私的人呢?
另外,任先生的解释本身就前后矛盾。既然老子认为“为了避免给自己招来忧患,最好不要身体”,那么为什么会紧接着又提出“只有把天下看轻、把自己看重的人,才可以把天下的重任担当起来”的主张呢?一会儿不要身体,一会儿又要看重身体,老子当不会在同一章中出现如此严重的抵牾吧。
实际上本章讲的主旨是“无私”。老子认为一个人之所以会“宠辱若惊”,根本原因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重。一个人如果达到无私(无身)的境界,把个人利益置之度外,他根本就不会因荣辱而受惊,甚至根本就不会有荣辱之感。更何况圣人“不争,故无尤”(八章),不争荣,哪里会受辱呢?而且只有这种无私无欲的圣人才能够治理好天下。这样解释,不仅全章浑然一体,而且与全书的思想也是一致的。
最后,我们再分析一下“贵以身为天下”和“爱以身为天下”的句式。很明显,“贵”和“爱”是互文,都作动词使用,而“以身为天下”则是它们的宾语。“以身为天下”的意思是“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去治理天下”或“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去为天下服务”,这也不会产生歧义。相反,把“贵以身为天下”译为“把天下看轻、把自己看重的人”,把“爱以身为天下”译为“把天下看轻、爱自己胜过爱天下的人”,则与原句意思全不相符。蒋锡昌深知这一点,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采取了颠倒词序的办法:“此数语乃倒文。正文当作‘故以身为天下贵者,则可以托天下矣;以身为天下爱者,则可以寄天下矣’。”(《老子校诂》)这么一颠倒,固然文从字顺,但这种随便颠倒原文的做法却难以服人。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解读】
关于“有生于无”,不少学者认为这是讲“无中生有”“无能生有”,也就是说,“无”是“没有”,而“有”是从“没有”中产生出来的。从绝对虚无中产生万物,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西晋的裴撰写《崇有论》一文,对这一观点进行批判。
更多的学者把“无”解释为“道”,因为大道看不见、摸不着,故称之为“无”。如果把“无”解释为大道,那么第二章中的“有无相生”就应该解释为“万物与大道相互产生”,这更是一种逻辑上的混乱,因此杨柳桥在他的《老子译话》中责怪老子说:“既主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又说‘有无相生’,他的思想体系是不够周延的。”在杨柳桥先生看来,“有生于无”的“无”是指作为宇宙本体的大道,“有无相生”的“无”是“有”存在的条件,于是老子在使用“无”这个概念时就自相矛盾了。
其实《道德经》全书中的“无”,除了用于“虚无”“没有”等本义外,其他指的都是空间,而“空间”正是由“虚无”引申而来。既然“有无”能够“相生”,那么现在强调其中的一面—“有生于无”,当然是可以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物质只有相对于空间才能存在,如果没有空间,也就无所谓什么物质。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只知道物质带来的好处和作用,而不注意空间带来的好处和作用,因此在第十一章中,老子就专门强调空间的作用,认为各种器物之所以有用,原因就在于它本身存在着“有”“无”两个道对立面,如果全是物质,而没有空间,那么物质就失去它的作用,器物也就没用了。老子把这一观点引入政治领域,就是要提醒人们不要只注意“无不为”的好处,还要注意“无为”的好处,“无不为”是以“无为”为基础的,就像物质是以空间为基础一样。具体到本章,老子强调有“无”才有“有”,是为他的有“弱”才有“强”的处世观服务的。
可以说,老子如此反复强调空间的作用,其最终目的仍是想通过自然现象来为他的政治主张、处世原则寻找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