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始元六年(前81),一场官方和民间就是否延续前朝国策展开的大讨论,在西汉都城长安举行,史称“盐铁会议”。汉宣帝时,桓宽根据会议记录进行整理,遂成《盐铁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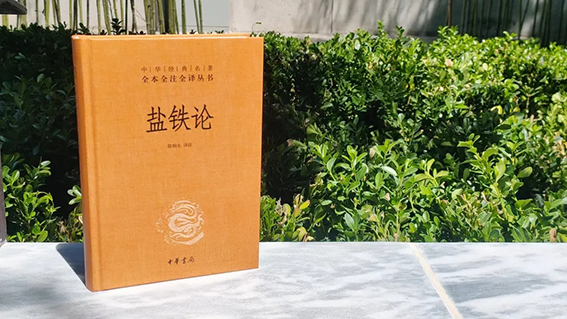
《盐铁论》
公元前81年,距离汉武帝去世才过去7年,而要求展开这场讨论的,正是汉昭帝——汉武帝的小儿子,时年14岁的刘弗陵。
昭帝小小年纪,而召开如此重大的会议,论改国策,绝非心血来潮。
武帝连续多年对外征战,建立了空前辽阔的疆域。但是,非常之功业,必然需要非常之代价。为了弥补战争造成的国库空虚,汉武帝推行了盐铁官营、均输平准、酒类专卖等等经济政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也给民间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武帝晚年意识到了问题,在著名的《轮台诏》里,说:“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在《资治通鉴·汉纪》的记载中,则表达得更明显:“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意愿已有,但武帝未及推动就去世了。忠实执行遗愿的,除了汉昭帝,还有顾命大臣霍光。
汉武帝曾经赐给霍光一幅画,画上,周公抱着周成王,接受朝见。武帝临终,指定刘弗陵即位,让霍光担当最重要的辅政大臣,也就是周公的角色。
这对“成王周公”组合逐步推动执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主张,对外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就是召开盐铁会议,讨论武帝时期的一系列政策。
会议以论辩的方式进行。论辩中,主张延续前朝政策的一方,是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代表的朝廷重臣,也就是《盐铁论》中的“大夫”及其团队;主张废止或调整的一方,则是以三辅地区举荐的俊逸之士(贤良)、州县举荐的人才(文学)为代表的民间士人,也即“贤良”“文学”。

盐铁官营等一系列经济政策,无疑是这次会议的讨论焦点,也为后世人们研究经济史、乃至了解经济运转规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大夫一方认为,盐铁官营利国利民,有益无害,还消除了像吴王刘濞那样的地方分裂势力;贤良、文学则力主取消平准、均输、酒榷制度,罢盐铁官营,他们认为这些政策是与民争利,造成国家空虚,富国安民的根本在于搞好农业。
双方的交锋,火星四溅,金句频出。
比如,关于怎样才能快速积累财富,大夫斩钉截铁: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意思是,致富在于筹划,不在于亲身劳动;获利在于地势优越,不在于努力耕作。
文学针锋相对:利在自惜,不在势居街衢;富在俭力趣时,不在岁司羽鸠也。意思是,获利在于自我珍惜,不在于地处街道要冲;致富在于节俭,努力按时耕种,不在于每年派官吏从事于羽鸠赋税的征收。
关于治国是否唯重农耕,文学坚持认为:衣食者民之本,稼穑者民之务也。二者修,则国富而民安也。大意是,衣食是民众生存的根本,种植和收割是民众的主要事务。这两方面做好了,就会国富民安。
大夫则主张,路径非止一条:贤圣治家非一宝 ,富国非一道。贤君圣主治理国家并非只有一种法宝,使国家富裕也并非只有一条道路。换言之,国家经营盐铁、酒类以及实施均输、平准,都是出于富国足民的目的。
用以托举这些金句的,是大量饱含历史经验教训的前朝往事,以及双方站在不同立场所获取的细节信息。今天的我们,如果单看这些句子,可能会觉得都有道理;但如果结合当时的内外形势变化去看待,便会做出一些带有倾向性的判断。就比如说,记录者桓宽自己,立场就站在贤良、文学一边。
这场持续了五个月的论辩,讨论的除了盐铁专营中心议题之外,还涉及新形势下对匈奴政策的调整,以及对商鞅、邹衍、李斯、晁错等人的评价,再到如何看待儒学价值、奢侈风气、官员贪腐、国家安全,乃至天子诸侯的园池是存是废,要不要遵守先王之道,什么样的人才是贤人,应该坚持王道还是霸道,等等等等。
双方看似地位悬殊,但都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贤良、文学一方仗义执言,指陈时弊,言辞之间处处流露处士横议遗风,昭帝和霍光的支持,也给他们增加了畅言的勇气;大夫一方,时常遭到不留情面的批评,难得的是,至多“默然不对”“悒悒不言”“勃然作色”而已,没有动用权势去压制对手,尽量以平等的姿态去讲道理。
舌战群儒的御史大夫桑弘羊,论辩过程中,同样有气得说不出话、需要丞相或下级帮腔的时候。会议开到最后,桑弘羊疲累之至,说了一句:“诺,胶车倏逢雨,请与诸生解。”
作为会议的官方代表,他要宣布散会,于是说:“就这么着吧,胶粘的车子突然碰上下雨,请各位散了吧。”
这位博学通才,居然用了一句歇后语来宣布会议的结束:“胶车倏逢雨——散了!”看似突然,而余味深长。
会议结束后,朝廷接受了贤良、文学的部分建议,废除了酒类专卖,而继续保留了盐铁专营和均输平准政策。
对于这个结果,桓宽表示惋惜,特意用“盐铁”二字作为书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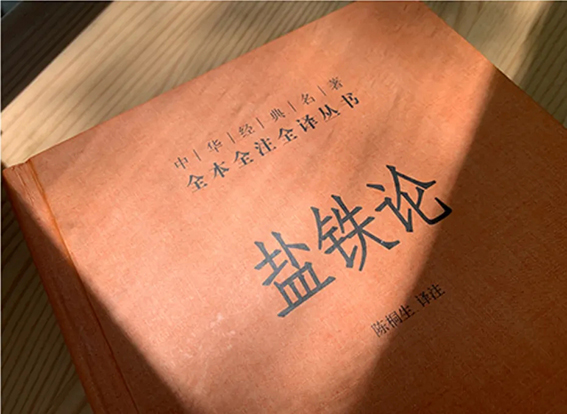
正因为这部书的存在,我们得以身临两千年前的顶级辩论会场,看到一系列围绕道义和利益、理想与现实、宏观与微观的精彩讨论。
围观这样的高水平辩论,可以启发今天的我们多从正反两方面去看待问题,避免偏激,不局限于表面的“对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