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把《聊斋志异》中的《瞳人语》当作劝惩教育小说看待。清代著名《聊斋志异》评论家但明伦说:“此一则勉人改过也。轻薄之行,鬼神所忌。”何垠说:“此即罚淫,与《论语》首论为学孝弟,即继以戒巧言令色意同。”他们的话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是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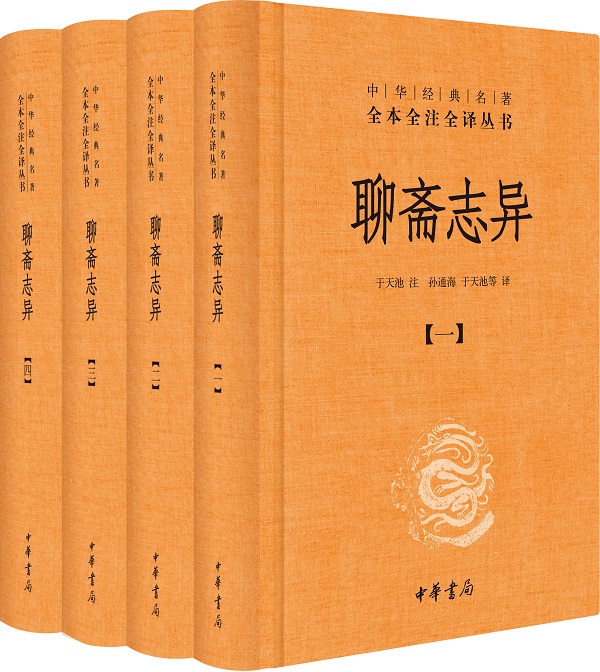
▲ 中华书局三全本《聊斋志异》
《瞳人语》叙述长安读书人方栋有才而轻薄,在清明节的前一天,他在郊区看见一个乘车的女郎长得非常漂亮,便尾随偷看。没想到女郎是芙蓉城的神女,神女发怒,神女的婢女痛斥了他,并撒了一把土迷住了他的眼睛。随后他得了白内障,双目失明。方栋痛自忏悔,请人给他持诵《光明经》。一年之后,在方栋趺坐捻珠时,听到双目的瞳人对话,它们由于失明感到憋闷,于是从鼻孔飞出去散步解闷。后来瞳人又嫌从鼻孔出去不方便,干脆抓破了左眼的白内障,两个瞳人一起居住在左眼。于是方栋的右目依然白内障,左目成了重瞳,视力比常人还要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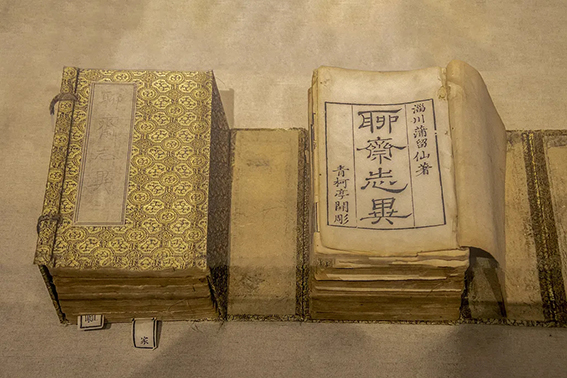
▲ 《聊斋志异》青柯亭版
这个方栋确实够倒霉的。站在现代人的立场,尾随看漂亮的女郎,似乎算不上犯什么大错,不就是看看吗?连性骚扰都算不上。那女郎不愿意让看也就罢了,撒把土让人家得白内障真是罚不当罪。但是,在封建社会,在明清时代,方栋又确实犯了“非礼勿视”的错误,按照“万恶淫为首”的原则,神女让他眼瞎,也还是薄惩呢!好在方栋受到惩戒之后,幡然悔改,念经持诵,终于得到神女的原谅。两个瞳人抓破了壁障从而恢复了方栋的视力可能正是神女的旨意呢!正如蒲松龄在“异史氏曰”中说的:“轻薄者往往自辱,良可笑也。眯目失明,又鬼神之惨报矣。芙蓉城主,不知何神,岂菩萨现身耶?然小郎君生辟门户,鬼神虽恶,亦何尝不许人自新哉。”
从教育劝惩的角度看,《瞳人语》体现了蒲松龄教育劝惩篇章的特点——其所重不在惩罚,而在强调自新。劝惩的目的是教育人和改造人(见于天池《论蒲松龄的教育思想与<聊斋志异>的教育精神》,《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3期)。从作品的结尾来看,士人方栋“由是益自检束,乡中称盛德焉”,的确反映了蒲松龄教育劝惩的良苦用心。

也许有人会问,《聊斋志异》中许多痴狂的读书人追逐女性都如愿以偿,像《青凤》中耿去病之于青凤,《荷花三娘子》中的宗相若之于三娘子,《辛十四娘》中广平冯生之于辛十四娘,他们的行为按说比方栋还要张狂,为什么他们能如愿以偿而方栋以失败告终并受到惩罚呢?
推究其原因,大概有三个方面:首先是读书人行为的界定。在蒲松龄看来,方栋的行为属于轻薄。到处追逐看女人,与专一追求一个女人的多情不同。方栋是“每陌上见游女,辄轻薄尾缀之”,这是轻薄不是多情。追求对象是已婚的新妇和未婚的少女也是不同的。对于未婚少女的追逐,不管男性已婚未婚,在蒲松龄看来都可以称作是多情,但追逐已婚妇女,则属于轻薄。《瞳人语》中的方栋和后面附录中的士人以及《画皮》中的王生都是追逐已婚妇女,所以因轻薄受到了惩罚。其次,《聊斋志异》中的读书人与少女的婚姻或恋爱是有层级的。其中读书人可以贫富不论,都是人间的人,但少女的身份却有鬼狐、人、神的等差。少女如为鬼狐,则为异类,她们不受礼法的保护,也不受礼法的束缚,士人对于鬼狐,可以自由恋爱,可以浪漫,而她们也可以逾墙相从,夜荐枕席,甚至“春风一度,各别东西”。假如少女是人间的女郎,就需要按照人间的礼法行事,不能越礼。人有男女之别,婚姻须经父母之命,《菱角》中的菱角和胡大成如此,《青梅》中的张生和阿喜也是如此。《王桂庵》中的王桂庵和《连城》中的乔生对于他们心爱的姑娘的追求不管多热烈,于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却永远是一道迈不过去的坎,蒲松龄写人间少男少女的恋爱总是围绕着这一界碑做文章。但如果少女是神祇的话,神女尊贵,地位在人之上,读书人与神女的婚姻或恋爱,是神俯就人间,赐婚赐爱,人完全是被动地接受,不能主动,不能有非分之想,否则就是亵渎神灵而要受到惩罚。《瞳人语》中的方栋假如尾随的是鬼狐或人间的少女,可能不至于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但他尾随的是“芙蓉城小娘子”,后果就非同小可。再有就是,假如我们对于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作品加以分期,那么,《瞳人语》大概属于早期的作品,而早期蒲松龄的作品较为正统,劝惩教育的味道比较重,没有中期、也就是他中年创作的故事那么充满孤愤和浪漫精神。《瞳人语》既然属于早期作品的行列,其有着浓厚的正统思想,强调“非礼勿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从另一种角度来看,《瞳人语》还是一个关于疾病题材的故事,一个根据眼疾生发出来的浪漫故事。
蒲松龄是一个自身多病又对于医术非常感兴趣的作家。他对于山区的常见病、多发病很有研究(见于天池《从蒲松龄的疾病说起》,《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3期)。白内障是一种常见的眼疾,但是,在古代,人们无法对于白内障的病因和病理进行科学解释。而蒲松龄的医疗思想中本来就具有巫医结合的因素,因此,他认为白内障的产生是由于违反了“非礼勿视”的道德规范,招致了神灵的惩罚。而念经忏悔,改过自新,神灵便给以宽恕,视力从而得到了恢复,符合自然物理。当然,不能认为小说中的描写就一定是现实中蒲松龄对于白内障眼疾的认识;但是,以蒲松龄当时的医学常识和他的巫医思想而言,他按照这样的逻辑编织故事顺理成章。
按照现代医学的解释,白内障是眼睛内晶状体发生混浊,由透明变成不透明,阻碍光线进入眼内,从而影响了视力。造成的原因除了主要是老年性的自然因素之外,某些内科疾病诸如糖尿病、肾病以及某些外伤也可以引起。但扬一把沙子就使眼睛得了白内障则有些夸张,不合医学原理。小说写两个瞳仁合并成一个,形成重瞳,更是将传闻和想象结合了起来。按照眼睛的构造,真正意义上的重瞳是不存在的。所谓重瞳,不过是眼睛中的瞳仁有斑块而已,是一种残疾现象。在中国历史上,见于历史记载的名人重瞳有三个,一个是舜,一个是项羽,再一个是李后主,都是以重瞳增加了他们神奇天赋的分量。重瞳既然从解剖学的立场上看是一种误解,那么由白内障的发生转变到重瞳,按照现代医学的观念更是天方夜谭。不过,蒲松龄的描写则有一定的合理和可称道的地方,比如,小瞳人从鼻腔出入,暗示眼睛和鼻腔相连,就合乎解剖学的原理。想象小瞳人抓破白内障而使得眼睛复明,也颇类似于后代早期治疗白内障的拨翳的方法。
不过,站在读者的立场上,《瞳人语》值得我们看重的既不是关于眼睛失明和复明的道德诠释,也不是那个时代对于眼疾治疗上的民俗说明,而是文学上的描写,是蒲松龄文学描写上的成就让《瞳人语》赢得了读者的喜爱。
《瞳人语》文学描写上的成就表现在哪里呢?首先是精确和生动。虽然从医学的角度,蒲松龄对于白内障眼疾作了荒谬的解释,但是从文学的角度,他对于白内障的临床现象却有着精妙的描述:
倩人启睑拨视,则睛上生小翳,经宿益剧,泪簌簌不得止。翳渐大,数日厚如钱。右睛起螺旋,百药无效。
我们不能不佩服蒲松龄精细的观察和惊人的表现能力。正是这种观察和表现,构成了《聊斋志异》相当一部分疾病题材小说的特殊魅力。假如我们联系《聊斋志异》中其他有关疾病类题材的描写,像《娇娜》中关于外科肿瘤的描写,《梅女》篇关于保健按摩的描写,《董生》篇针灸的治疗,《医术》中对于奇方秘术的调侃,谁能说《聊斋志异》不是开辟了一个新的题材领域呢!在文言小说史上,蒲松龄可以说是第一个尝试以疾病为题材表现人生的文言小说作家。
其次,《瞳人语》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童话的意趣。假如是一个平庸的作家,对于违背“非礼勿视”的惩罚,也许就止于让人失明而已,不会对失明的过程作进一步的描述。但蒲松龄不是一般的作家,他对于白内障病理现象浮想联翩,把白内障这种眼疾幻化成动态的小瞳人的活动:
忽闻左目中小语如蝇,曰:“黑漆似,叵耐杀人!”右目中应云:“可同小遨游,出此闷气。”渐觉两鼻中,蠕蠕作痒,似有物出,离孔而去。久之乃返,复自鼻入眶中。又言曰:“许时不窥园亭,珍珠兰遽枯瘠死!”生素喜香兰,园中多种植,日常自灌溉。既失明,久置不问。忽闻其言,遽问妻:“兰花何使憔悴死?”妻诘其所自知,因告之故。妻趋验之,花果槁矣。大异之。静匿房中以俟之,见有小人自生鼻内出,大不及豆,营营然竟出门去。渐远,遂迷所在。俄,连臂归,飞上面,如蜂蚁之投穴者。如此二三日。又闻左言曰:“隧道迂,还往甚非所便,不如自启门。”右应云:“我壁子厚,大不易。”左曰:“我试辟,得与尔俱。”遂觉左眶内隐似抓裂。有倾,开视,豁见几物。喜告妻。妻审之,则脂膜破小窍,黑睛荧荧,才如劈椒。越一宿,幛尽消。细视,竟重瞳也,但右目螺旋如故,乃知两瞳人合居一眶矣。生虽一目眇,而较之双目者,殊更了了。
你看,眼睛里有小瞳人,它们“大不及豆”,说话的声音“小语如蝇”,从鼻中爬行像钻隧道,使人“蠕蠕作痒”。飞回眼眶的时候像“蜂蚁之投穴者”。左右眼睛的小瞳人联袂而行,一起坐卧。它们活泼好动,不甘寂寞,经常到花园中游玩。失明的原因是它们被关闭在黑漆的门里,复明的原因是它们嫌憋闷,把那黑漆的门——白内障壁垒——抓破了。两个小瞳人住在一起后,人虽然成了独眼,但视力觉得比前更强了。
这是多么好的童话情节啊!著名批评家李长之曾经在上个世纪50年代首次注意到蒲松龄的作品具有儿童文学的色彩,他说:“有人说,中国在‘五四’以后才有儿童文学,好像古典文学作品中就没有这一项似的。这恐怕不对。我以为《西游记》就已经是很好的儿童文学,我曾试着给小孩子讲,大概从五六岁到十几岁都很欢迎的。孙敬修同志在广播电台对小朋友讲《西游记》,小听众也十分热心。适合儿童心理,儿童又爱听,这就是好的儿童文学。蒲松龄写的《聊斋》也同样包含有很好的儿童文学。”“蒲松龄有可爱的童心,这是他写儿童文学成功的最大原因。他那美丽的幻想,又不只表现在上面所提到的几篇而已,乃是几乎贯穿在全书,构成了全书的魅力之一的”(李长之《蒲松龄与儿童文学》,《中国古典小说评论集》,北京出版社,1957)。李长之的批评的确是很有眼光的。可惜的是,蒲松龄的这种童话描写,只是部分的,而非整体的,并且是限制在儒家说教的框架下,其中的童话色彩没有得到充分的渲染和展示,我们只能认可《瞳人语》具有童话的情节,而不能直然认可它是童话故事。假如蒲松龄能够摆脱儒家传统道德伦理的束缚,《瞳人语》和《聊斋志异》中的其他带有童话色彩的小说的成就一定会更大些。
《瞳人语》在《聊斋志异》中是一篇较为特殊的小说:按照《聊斋志异》的叙述逻辑,男主人公方栋“颇有才名”,女主人公“红妆艳丽”,应该发生一番缠绵悱恻的情爱故事才是,但是小说简直有些“多情反被无情恼”的味道。不过,它又不乏浪漫的情调,这是另一种浪漫的情调,是一种带有童话情趣的浪漫。这种浪漫的童话情趣在中国的古典小说中很罕见,但在《聊斋志异》中却不乏体现,只是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罢了。这种浪漫的童话情趣,同蒲松龄以真为美的审美理想相联系,同蒲松龄特殊的生活经历和浪漫的文学表现风格相联系。而这种童话浪漫情趣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不能怪蒲松龄,是中国文化大背景大环境限制了他。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06年第8期



